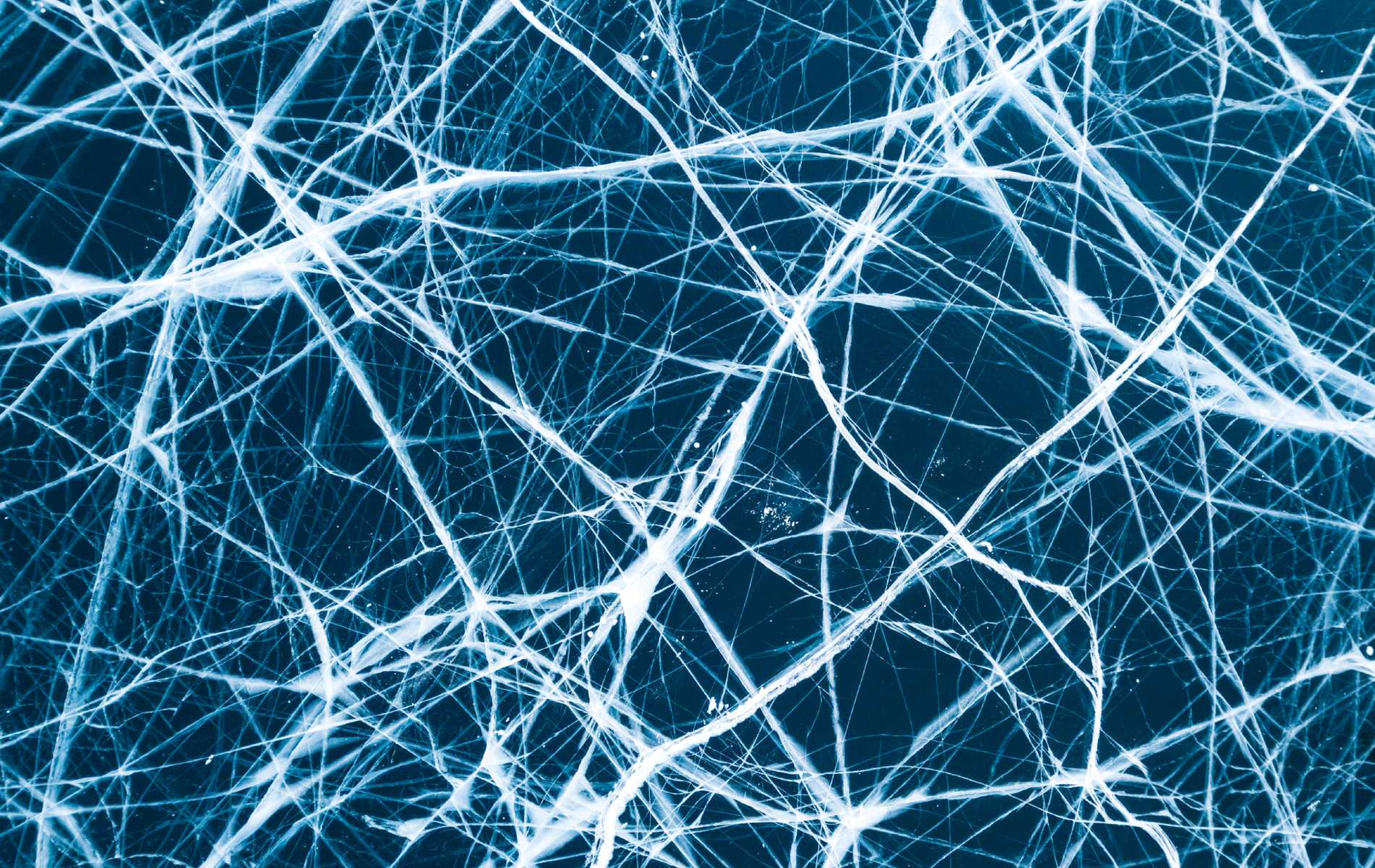2020年年中,许煜在洛杉矶与Noema杂志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畅谈,探讨比较技术哲学反思的新路径。原文为英文,本译文得到了许煜先生的亲自审校,深表感谢。
为了超越西方的现代性和当前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必须反思非欧洲的思想和存在的方式如何能够思考技术的发展。
I. 东方的宇宙技术和西方的宇宙技术
加德尔斯:你在作品中强调,基础性宇宙论产生和塑造了不同的文明。你所说的“宇宙技术”是什么含义?
许煜:或者我先解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概念。由于我们的科技创新正通过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等方式挑战着历史的限度,所以重新审视宇宙技术的多样性以及科技如何与世界观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150年里,中国的现代化主义者热情地接受了西方对技术的定义,即用以建立人类对其他一切的统治的工具。然而,为了超越西方的现代性和当前的全球现代化模式,我们必须反思非欧洲的思想和其存在方式如何能够思考技术的发展。
这项任务需要从当前技术发展的角度,对东西方思想史进行全新的诠释。我试图通过“道”和“器”这两个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范畴间的动态关系来理解中国的宇宙技术:“道”是一种宇宙万物生成的逻辑,“器”则指工具或器具。道和器一同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纵观中国历史,道与器的统一构成了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与西方相比,这种统一既推动又限制了中国的技术发展;在西方的现代时期,技术是由工具理性所驱动的,工具被塑造成征服自然而不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手段。
当今仍是如此,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之间的差异。现代西医通过将科学机械地应用在身体上来治愈疾病;传统中医试图通过促进身体内部的和谐来治愈疾病。中国传统医学使用的术语与中国传统宇宙论相同——例如互补对立的阴阳,或是通过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流动的,我们称之为“气”的能量。
加德尔斯:当我们听到“道德”一词时,它暗示着一种公平和正直的生活准则。你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你所讲的道器合一的道德是什么意思吗?
许煜:中国古代的道德并不是遵守行为准则的义务。对古人而言,道德——汉语中指“德”(美德)与“道”的和谐共存——指对天地之善的肯定和欣赏。
这在《易经》中清晰可见,《易经》中的天地即“乾坤”,两者都能够决定和塑造伟大的人格。对《易经》开篇的一种解读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的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处世,也应像天一样,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
于儒家而言,成为圣人就是知天命,因为尽管上天在不断变化,但开悟的圣人能够诠释其道德内涵,从而达到天人的和谐。道家将这种具有创造性的矛盾肯定为道与德,对他们来说,道德实际上代表着纯朴。
道既非虚无,也非存在,而是维持对立统一性的原则。它是维持对立面之间统一性的循环运动:在宇宙学中,是“无”和“有”之间的统一性;在形而上学中,是“体”和“用”之间的统一性;在人生哲学中,是“天”与“人”之间的统一性;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宇宙技术中,是道与器的统一性。
像中国人一样,古希腊人也看到了这些对立的存在。然而,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希腊人看到的是这些力量间的不连续性或矛盾性,而没有看到统一性或和谐性,这种差异在几个世纪后仍旧存在。
中国思想中的目的论所追求的不像西方思想中那样,终点在不断再生的宇宙本体中,而不在我们可以通过感官发现的已知现象世界里。
II. 生成的关系性变化
加德尔斯:所以在道教、儒教和日本神道教中,人类与宇宙或自然秩序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意识——不是人类与自然或他人之间的分离,而是万物的基本统一?
许煜:是的。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人们可能会说,中国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关系性的,而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思想根本上是关于作为实体的存在。
在西方哲学中,本质与偶性之间具有一种张力,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如果存在是关系性的(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偶性, ta pros ti)——那么一个存在就依赖于其他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将很难对其本质或实质进行定义。
谈到这种不兼容性,我们可以说,东方思想的根基在于关系,而不是追求绝对或本质。确实,在他的《论文字学》中,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比较了西方的表音文字和中国的象形文字,并得出表音文字与实体(黑格尔)相关,而中国的象形文字则是关系性(莱布尼兹)的结论。
英国生物化学家、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他对中国及其技术的研究中,把这种关系感应翻译成了“共鸣”。主体与宇宙之间的这种共鸣是道德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不遵从这种共鸣,那么他(或她)就是在违背自然。在此,自然并不是指外在于人的环境,而是事物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方式。
一些哲学家,特别是当代法国思想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认为中国思想中没有本体论或关于存在本质的形而上学。因此,关于Being或存有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未像在西方那样受到重视。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在这个尺度上进行的概括(generalization)难免遭遇例外,我们不能视其为原则,而是进一步思考的邀请。在此我们或者可以说,中国哲学中没有我们看到的西方对存在或永恒形式的追求,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使事物是其所是的永恒实在,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更具实证主义的“形状”或形式。中国哲学全是关于生成的关系性变化,而不是追寻某种本质存在的特定形式。
在西方,我们可以把绝对看作某种终结或终极现实。相应地,可以认为我们的知识在朝着这个目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前进。但在中国思想中很难找到这样的绝对。道家认为,思考什么最大、什么最小、什么是绝对的、终点在哪里等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总有超越这一切的东西:道,也是创造和再创造出我们已知更大或更小的事物的不断生发的过程。
因此,中国思想中的目的论所追求的不像西方思想中那样——因为它始终受天地无常的影响。目的从来都不是一件可以确切实现的事情。终点在不断再生的宇宙本体中,而不在我们可以通过感官发现的已知现象世界里。
我们已不再处于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所描绘的纯机械时代,而是一个崭新的机器时代。机械装置预设了线性的因果关系,而伴随着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生成有机体”,每个开始的终点将是另一个开始的起点。
III. 启蒙的终结
加德尔斯:海德格尔认为控制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因为通过系统内部的反馈回路,有机体和机器、客观和主观将能够结合在一起。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指出,现在的机器可以像人类一样,通过从意外的偶然性事件等经验中的学习来适应环境,因此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启蒙的终结”,或是人本哲学的终结。他认为,不是启蒙哲学催生了西方的技术统治,而是人工智能推动了对新哲学的探索。你怎样看待这些结论?
许煜:由于海德格尔读了美国哲学家、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其他控制论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理解通过再生反馈回路将有机体的思维同机器结合起来的深刻含义。如此一来,一位西方思想家可以被视为接近中国的宇宙论氛围。当海德格尔谈到形而上学的终结时,所指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过基督教,一路传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的终结。
在著名的1966年《明镜》周刊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中,当被问到哲学将被什么取代,他的回答是:“控制论。”在德语中,“终结”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成就”、“实现”或“完成”。所以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控制论技术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实现。
技术能力最终体现在了控制论和后来的通过反馈回路、学习算法可以像有机体一样适应环境的人工智能中,克服了活力论(vitalism)和机械论的对立。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用“生命冲力”(élan vital)的概念反对机械论。维纳的控制论认为这种反对是错误的,因为控制论机器克服了这种反对观点。换言之,在将人类的思维能力与机器进行对比时,现代哲学曾依赖于有机的活力论概念,而控制论的主张是要克服这种二分法。
为什么控制论有如此之大的变化,而不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说的早期自动化机器?对海德格尔来说,控制论是理解存在的一种更为高级和有机的形式,但它仍代表着现代性在技术和机械上战胜了自然。从这个层面讲,控制论就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实现与终结。
控制论的递归性和人工智能的学习回路实际上代表了这种对形而上学的超越。递归性不再是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的工厂中观察到的自动化机器的机械性重复;其特点在于循环运动,即返回自身以肯定自身,而每一个运动都是对偶然性开放的,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它的独特性。
这种递归性的概念对应于我们所理解的灵魂。灵魂可以回归自我,以了解并决定自我。每遇到新的机会而离开自我,它就会在我们称之为记忆的痕迹中实现自我。偶然性这种新的信息引发了个体化的过程。正如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言,“信息是造就了差异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谈到“心灵生态”,每一个存在的独特性都是由这种递归性和偶然性构成的。
加德尔斯:说到偶然性,不得不提到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这场疫情让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都踏上了一条不同的轨迹,它开启了我们从注重日常习惯到对待微生物的认识等在内的一整套全新的递归循环。
许煜:当然,是这样的。但回到基辛格,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我们还可以从技术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观点。百科全书派相信机械工具有着无限改进的可能性,他们对进步持有的乐观态度,推动了启蒙运动这样一个机械化的时代。我们已不再处于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所描绘的纯机械时代,也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热力学机器时代,而是一个崭新的机器时代。机械装置预设了线性的因果关系,而伴随着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生成有机体”,每个开始的终点将是另一个开始的起点。
加德尔斯:伴随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它似乎明显变得更像道家了。海德格尔所寻求的新开端其实早已已在东方出现,但他又将研究投向了欧洲思想的早期传统。
这种前苏格拉底式的探索,海德格尔对内在真理的思考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过程中,他明确只有在“家园”和“民族精神”的背景下,才能构成“存在本身”和“存在总体”的内在真理,这与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观点遥相呼应。也同你对多元宇宙技术和道教宇宙观的想法是一致的。
许煜: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把海德格尔的研究项目与我所说的宇宙技术联系起来,尤其是当他想把古希腊的技术含义重新表述为存在的去蔽,即希腊人所说的真理。基于当地朴素美德的思考是宇宙论气氛的动力。然而,对我来说,这种关于当土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拒绝改变、拒绝进步或任何形式的回归传统主义;相反,旨在从本土视角和对历史的新理解出发重新解释技术,但它必须拒绝成为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这也是危险的所在。但“危险之处,拯救的力量也在生长。”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个与启蒙哲学相反的方法:根据差异来碎片化世界从而达到共同,而不是通过一个假定的绝对来普遍化世界。
IV. 新轴心时代
加德尔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作的“轴心时代”中,包括中国儒家思想、印度奥义书和佛教、荷马希腊和希伯来的先知在内,所有伟大的宗教和伦理体系都同时出现在一个不同步又几乎互不关联的世界中。那么,现在所有思想体系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历史上,趋同的线索诞生了新的分歧。正如我们所讨论的,人们已经开始寻找现代性之后的新开始。西方及其哲学所展开的全球蔓延现在已经达到极限并正在分裂;对立统一正在转变。如果我们处在“哲学思考的新状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许煜:正是由于这种普遍化和趋同,我们正处在你刚刚说的“新轴心时代”的开端。现在的问题不是“会发生什么”,而是“能发生什么?”对此进行哲学思考,需要从“不可能”开始去思考“什么是可能的”。
为了探讨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西方宇宙技术与中国宇宙技术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并被同化为一种普遍的单一关系。在西方,对中国宇宙技术的思考,往往停留在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技术进步所作的比较。
另外,我反对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和彼得·蒂尔(Peter Thiel)等超人类主义者的技术想象。我们需要设想其他的可能性、分叉以及分裂,而不是目的论般地向“标准的”西方奇点靠拢。新的开端应当有多个由分裂所开启的起点。
加德尔斯:与其加速竞争来实现奇点的普遍化,你认为唯有抵制它才能带来崭新的开端?那中国的宇宙技术会是什么呢?
许煜:我称之为道德秩序和宇宙秩序的统一,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征服自然意义上的技术活动。技术存在于一个更为巨大的现实中。忽视这一现实将导致对技术的完全控制,从而导致对特定生命形式和思维方式的控制。其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一套植根于非欧洲思想的宇宙技术如何为理解科学“进步”发展出一个全新的框架。
重新思考和阐明技术的概念能够让我们发展出一个新的方向吗?它不必然是更为先进的技术,而是发现和发明新的认识论和知识以应对人类世时代的危机,不限于气候变化。
加德尔斯:还有什么其他的思考吗?
许煜: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启蒙时代。启蒙运动表明,哲学是变革的基础,因为哲学改变了政治、社会、道德、教育、宗教、国际关系和法律的基本原则。
这种哲学概念必须向面向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的可能性转向。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个与启蒙哲学相反的方法:根据差异来碎片化世界从而达到共同,而不是通过一个假定的绝对来普遍化世界。随着现代性的崩塌,一部新的世界历史必将出现。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6月19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