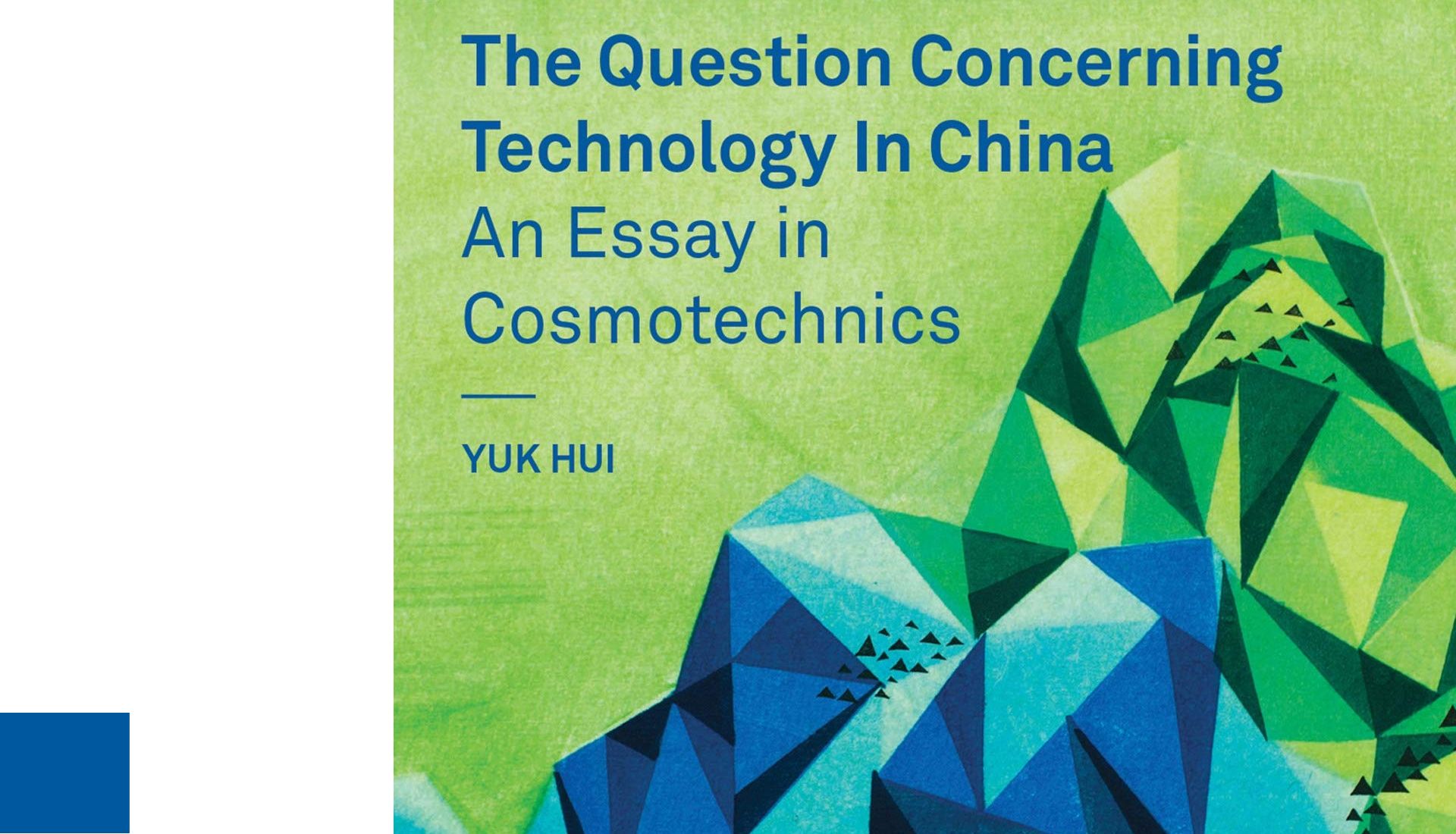没有一个西方人像李约瑟那样,为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做的种种贡献而欢呼。
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从公元前5世纪到16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明。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传统比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知识传统都更了解自然,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然而到了16世纪,中国开始失去它的领先地位。为什么中国没能保住它的主导地位,把科技优势拱手让给了欧洲?
这个问题令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1900-1995)为之着迷。没有一个西方人像他那样,为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做的种种贡献而欢呼。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series),1954年开始出版,至今仍在延续(已出版27卷)书。在著名历史学家西蒙·温彻斯特的《爱中国的人》(2008)中,它被描述为可与亚里士多德作品相媲美的中国巨著。
李约瑟和海德格尔
李约瑟的写作计划始于1937年,与一位来自南京的博士后的邂逅,让他意外地接触到了一个比西方任何一个文明都更古老、更庞大、更延续的文明的丰富性。作为西方科学的热心信徒(坚信西方科学具有普遍性),李约瑟开始发掘中国与欧洲的发现与发明之间隐藏的连续性。今天,李约瑟研究所在亚洲是更广泛意义的科学(包括技术与医学)历史的主要研究中心。
李约瑟多卷本计划在英国开始的同一年,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在给德国工程师的一系列演讲中发表了《技术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一文。这篇短文针对西方对其技术和科学优越性的颂扬提出了异议,对现代技术哲学批判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现代科学的真理既不是对迷信的排斥,也不是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发展。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现代科学的真理既不是对迷信的排斥,也不是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发展。
是的,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再到电力与核反应堆,科学应用的技术力量通过减轻工作负担、增加物质财富、加速运输与加强通讯等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人从他们的产业劳动中异化出来,破坏了社会文化的稳定,并让人们感到无家可归。关于美好生活及其意义的社会传统共识破裂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权力的追求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技术维系的全球主义似乎助长了未加修饰的世界主义,而这种世界主义可能导致反对的政治运动(例如,见特朗普主义)。
海德格尔充分认识到二十世纪的巨大工程成就。但是他认为比人类经验的物理转化更为根本的是文化假设与实践的蜕变。对于现代人类,关于实在本质的基本信念已经发生改变。在前现代传统中,人类将自然理解为一个终极稳定的秩序,并渴望与之和谐相处,而现代世界观将自然视为“为人类使用和便利”(for the use and convenience of man,引用1828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皇家宪章》)而提供的大量资源。时至今日,自然在西方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唤起崇敬与好奇的给定,而是一个由人类创造者的多样需要和欲求所重建的东西。只要创新胜过沉思,人们就会发现越来越难以欣赏他们所拥有的东西,难以从世界的特殊和美丽中获得根本的快乐。
技性科学
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2016)一书中,许煜这位年轻的中国计算机学家和哲学家,大胆地尝试重新审视李约瑟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于任何一个有兴趣去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种种哲学挑战和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的崛起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了。
在香港长大,许煜掌握了流利的汉语和英语。在获得计算机工程学位并在该领域从业之后,他前往欧洲求学,在那里先后精通了法语和德语(期间还学习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许煜在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德·斯蒂格勒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后者的三卷本《技术与时间》既深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也对之提出了挑战。凭借其技术和哲学的专长,许煜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计算机编程历史发展的本体论研究,2016年出版为《论数码物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一书,由斯蒂格勒亲自题写序言。献给斯蒂格勒的《论中国的技术问题》,是对世界的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突变展开的一次更深入地探讨。
许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人们接受存在多个自然,那是否有可能想到多种技术,它们不仅在功能和美学上,而且在本体论和宇宙观上也各不相同?”
该书旨在反思技术,其前提基于并发展了这样一种理念,即自然不是某一事物:自然是共同构建的,因而是可变的,并且这种可变性在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的技术中体现出来。尽管科学家假定宇宙在他们的理论和实验发现的基础上总是相同的,但是这些发现本身体现了一种自然实在变动不居的观点。就连李约瑟也承认,与现代西方相比,中国文化(关于宇宙起源以及人类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有着不同的宇宙观。在这样的背景下,许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人们接受存在多个自然,那是否有可能想到多种技术,它们不仅在功能和美学上,而且在本体论和宇宙观上也各不相同?”
两个例子
作为这种差异的一个例证,在加州淘金热期间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引进了人力水车,为了将水泵入干涸的河床进行淘金。这种做法有赖于工人之间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对于个人主义的美国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有人在拨水,而其他人在淘金,所有人都平等分享采矿利润。一个典型美式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具有技术后果。
举一个更具推测性的例子,中国书法不仅仅是在美学上不同于拉丁字母。它确立了一种理解实在的方式,与海德格尔所谓的“在世存在”。中国书法作为一种以书面文字代表事物的符号系统,使世界上的实在优先于抽象的人声。中国的书写艺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关涉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修养的形式。
中国的神话对技术的解读是截然不同。——没有人类对天的反抗,只有参赞天地之化育,并在世间培养和接受审美、仪式与共同的欢乐。
这些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处于其中的人的能动性是如何产生的?许煜注意到神话中关于“技术”起源的不同描述,抑或是技术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西方的希腊和希伯来传统中,技术在文化上被认为是对众神或者上帝的一种反抗。普罗米修斯窃取了火的技术,并把它交给了缺乏天赋的人类,而因此受到宙斯永恒的折磨。巴别塔是一次技术上的努力,以期到达天堂来蔑视上帝,而人类受到的惩罚是多种语言,使彼此之间不再能够相互理解。
正如许煜所指出的,中国的神话对技术的解读是截然不同。既没有普罗米修斯的盗窃也不存在人类对上帝的反抗。取而代之的是古代部落的三位神话领袖:半人半蛇的女娃;她的半人半龙的夫兄伏羲,以及主宰农耕并后来掌管灶事的神农。这三位共同创造了人类,并为人类提供了诸如火这样的工具。人类被视为介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自然组合。没有人类对天的反抗,只有参赞天地之化育,并在世间培养和接受审美、仪式与共同的欢乐。
宇宙技术
许煜创造了“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一词,用来描述“通过技术活动来实现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这是任何神话都所蕴涵的。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将宇宙观与关于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的文化信仰联系起来,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现代技术所摧毁的。
在致力于赋予中国发明传统价值的过程中,李约瑟提出了现已成为“李约瑟问题”的问题:在16世纪以前,科学技术比欧洲先进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技性科学?然而,他未能注意到许煜所辨析的神话差异,而将中国的失败归因于一系列历史上的偶然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和宗教。除此之外,许煜还认为,海德格尔从未考虑过西方工程学中一个简单差异的含义,即它(技术)产生于军事,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器”(技术)和“工程”是与农耕和稳定的、定居的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技性科学的哲学酸性,过滤掉了与地方特殊性的联系,倾向于淡化关于善的社会共识,而追求现代科学本身或个人主义自由。安·兰德的极端自由主义在风险资本资助的工程企业家中蓬勃发展,这是偶然的吗?
许煜的两个重要反思
在对自己的构思计划做过了详细介绍之后,许煜将他的反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寻找中国的技术思想”,探讨了三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中“器”与“道”(宇宙秩序)之间的关系。这种广泛的对话为中国哲学带来了新的参悟,多个世纪以来(儒释道的不同观点)在中国哲学内部存在许多排序,同时也促进了与西方主要哲学传统以及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之间的对话。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原创的、具有挑战性的成就,今后在全球语境下考虑技术的任何努力都需要加以考虑。
第二部分“现代性和技术意识”,借鉴许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阐述,重新审视西方的技术哲学,并为中国紧随西方之后的当代趋势提供替代方案。许煜的挑战不仅是针对西方,也是针对中国。
许煜反复强调镜像问题:在西方,技性科学的哲学酸性[1],过滤掉了与地方特殊性的联系,倾向于淡化关于善的社会共识,而追求现代科学本身(至少在科学共同体的少数中)或个人主义自由(在非科学共同体的多数中)。安·兰德的极端自由主义在风险资本资助的工程企业家中蓬勃发展,这是偶然的吗?
在中国,从明朝开始,一种富饶的文化就无法抵御(由科技进步武装起来的)欧洲帝国主义,它一直在努力寻找保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许煜建议,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中国的努力都值得被给予比现在它所得到的更多的思考。他显然是想吸引那些试图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特别是当代世界的社会评论家和科学技术哲学家。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会就充满了对科学传播、对科学知识的不信任与排斥,以及对公众支持科学研究的攻击等问题所涉及困难的讨论。
然而,除了哲学家之外,还有谁会积极地成为许煜的观众呢?我认为,任何人都关心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对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感兴趣。
与海德格尔深入地追问技术的观点相比,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和工程师,甚至许多普通的西方人都更接受李约瑟的科学观,致力于理解普遍规律和为人类所占有的自然的最佳解释。因此,大多数读者可能会发现,许煜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持续介入,充其量只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张力。与此同时,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研究或制定科学政策的人,越来越认识到科学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征。例如,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会就充满了对科学传播、对科学知识的不信任与排斥,以及对公众支持科学研究的攻击等问题所涉及困难的讨论。
布鲁诺·拉图尔
正如气候变化等挑战所充分说明的那样,技性科学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结合)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从而促成对自然的新看法。一些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政治批评甚至(无意中)加入了实在的社会建构科学论理论,使循证决策边缘化。换言之,只要科学知识是通过社会和技术手段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发现”来构建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就会主张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构建事物。
当拉图尔向对话者询问中国人的看法,这些可能有助于在自然和文化持续变化的情况下实现许煜所说的宇宙技术生活时,却经常出现目的相左或沉默的尴尬的情景。
对此,激进地挑战科学家自我形象的法国科学论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最近也开始为科学辩护。正如他最近在《科学》杂志上的一次采访中所概述的,他的使命是“重新获得一些科学的权威,这与我们开始进行科学论研究的初衷是完全相反。”作为这一尝试的一部分,针对人类状况的突变,他在2017年出版的《面对盖亚:关于新气候制度的八次讲座》一书中进行了最广泛的探索,拉图尔一直在实践他所谓的对世界多种生存方式的哲学上的外交接触。
2017年,拉图尔访问了上海和北京,邀请中国同仁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有一次,许煜也在参与者之列。但作为一名观察者,在聚会上我发现他们非常不满意。不清楚拉图尔是否做了足够的功课来避免西方的东方主义投射[2],或是抵制中国的西方主义。拉图尔很难弄清楚他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但他似乎在要求中国知识分子为他自己的“重新描绘”世界的计划作出贡献(以便更好地研究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而未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独特性,或者当代中国人经常想模仿西方的方式。
全球化需要跨越历史、文化和技术范畴的思考和论述。阅读许煜的书可以是一个警醒的开始,但这还不够。
当拉图尔向对话者询问中国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有助于在自然和文化持续变化的情况下实现许煜所说的宇宙技术生活时,却经常出现目的相左或沉默的尴尬的情景。拉图尔想从中国学者那里得到他们不准备提供的东西,而中国学者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拉图尔最著名的是关于复杂社会关系的学术理论)更感兴趣,而不是他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
对于任何想要深入而认真地反思世界经历的人来说,包括全球化的社会动荡、生物多样性丧失、核扩散、气候破坏以及人工智能扩张,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的重大挑战,不仅仅是西方或东方的技术资源能够轻松地独自应对。全球化需要跨越历史、文化和技术范畴的思考和论述。阅读许煜的书可以是一个警醒的开始,但这还不够。正如许煜本人所指出的,他的目的只是为我们都需要更加认真对待的诸多想法敞开一道又一道门。
王誾 | 译
李贺 | 编
本译文系中文首发文章,得到了2020-2021博古睿学者许煜老师的亲自审校;翻译时,中国人民大学王誾博士亦多次向米切姆教授请教翻译问题,均深表感谢。英文原题Varieties of Technological Experience,发表在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4, no.4(Summer 2018):89–92。
[1]译者注:米切姆在这里用“酸”打了个比方,正如酸会侵蚀金属表面表面,在某些材料上,它通过分解所有的分子键来完全溶解它们,技性科学也具有腐蚀性,它打破了传统文化与当地紧密联系的方式。现代的技性科学作为一种同样的建筑材料,已经把一切都变成了混凝土,世界各地都是如此。虽然混凝土可以做成像木头一样,给人一种延续中国传统建筑的感觉,从而创造一种让人产生错觉的物质文化,可那仅仅是外表,是一种伪造的、断裂的传统。
[2]参见卡尔·米切姆. 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 [J]. 哲学动态, 2021: 1, 25-28.
(授权发布,未经允许请勿转载)